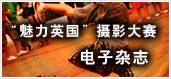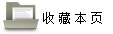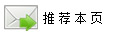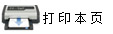撰文/王绶绾
我的
留学时期是一段“大浪淘沙”的年月。同龄先进者有过许多震撼人心的佳作,珠玉在前,令人深感有景道不得。于是只能在支流上集起一些回忆的片段,当作火红年代的一个陪衬吧。
中关村诗社的诗友中多中科院老者,一度谈起“诗与科学”,惊奇地发现许多人都曾有过熔诗歌与科学于一炉的“宏愿”。这也引起了我对当年
留学生涯的一个片段的回忆……
在夜色沉沉的大地上
我的斗室和原野合为一体
我化作了一根琴弦
在喧响的、宽阔的共鸣之谷上张起--勒内·玛利亚·里尔克
(杨武能译)
我第一次读里尔克的诗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,读的是英译本。很喜欢,但不很懂,有些朦胧。有几首写夜的诗感受颇深,原诗现在背不出来了,记得有一首写城市里的夜,写到远处楼房中婴儿的啼声,使人立即感到了沉浸在黑夜里的一片楼群何等寂静,而这寂静里又充斥着何等的生命气息。还有一首,前面引的是它头一节,是写郊外的夜。当时也曾引起了我的共鸣。
这是50年前的事了。那时我在伦敦大学天文台,地处伦敦西北郊,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阔,一条公路从伦敦伸过来,很宽很直;白天望过去,沿路的车像是一阵阵连发的火箭炮,频频交火。黄昏后,夜色罩下来,朦朦胧胧,路就像是一条笔直的运河,把岸两旁脉脉的思绪送往天的另一边。
当时的伦敦大学天文台人不多,几个年轻人,我也在内,合作得很好,常常在一起工作到天黑。一天下来,大家松一口气,喝一杯热茶,海阔天空,什么都聊,算是“积极休息”。M是我们中间的音乐家,有时兴起,就为大家拉一段小提琴。他从小练琴,拉起来很投入。不过不论什么曲他都只拉几个片段,余下的他说他“进不去”,全省掉了。大家取笑他缺乏完整性、全面性,不符合科学原则。他却说音乐对应的是心,科学对应的是脑,拉提琴时就是会彻底忘掉科学。于是有人就攻击他把帕格尼尼、克莱斯勒的“心”全撕成一片片了……这种争论自然不会休止,每回都只是因为天黑了要回家才告暂停。
这些当然都是友好的玩笑。其实,我完全理解M。科学追求认知,艺术捕捉感受,两者是人生多面体中两个最光彩的面。我理解M,还因为那时我对学诗写诗也很投入。在天文台我常常独自操作望远镜到深夜,这使我拥有了许多学诗写诗的夜。那是郊外“星垂平野阔”的夜,是进入里尔克诗中“宽阔的共鸣之谷”的意境中的夜。
M的话是对的。许多以往读过的诗会对应于此时此地的“心”的感受。记得一个初秋之夜,四五个小时的观测刚结束,走出观测室时,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,小立片刻,正是“庭户无声,时见疏星渡河汉。试问夜如何,夜已三更,金波淡、玉绳低转,但屈指、西风几时来,又不道、流年镜中偷换”。牵起一缕乡愁!我那时离家已经5年。这是东坡改写的词,本是写一对贵族恋人,但是我和M一样,只掐下我感受到的片段,借古人的酒,浇自己胸中的块垒。东坡也许没有想到过他的词会引出这样的共鸣。但我认为艺术就是会有这样的作用的。一百个导演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;贝多芬的《月光奏鸣曲》是在热恋中作的,“月光”则是多年之后一位评论家根据自己的感受起的标题,而这个标题自此与曲同在。我很欣赏音乐论述中用“演绎”一词来表达指挥家和演奏家对乐曲的处理。确切地说,作曲家是用乐曲演绎了他自己的感受,演奏家则用他的演奏演绎了作曲家乐曲中的表达,而听众则用自己的感受演绎了演奏家的演奏。你可以有你的演绎,我可以有我的演绎,感觉是多样化的,正如人生的多样化。这当然不能以衡量科学的那种严格、精确的尺度来衡量。难道不是艺术的多样化才使得文明社会中多角度、多层次的
生活如此丰富多彩?
夜深人静,正可以和古今诗人“讲求”艺术效果。拿“静的境界”来说吧,也许深夜里许多人都会感受得到,但如何表达出来?读王维的诗,觉得“雨中山果落,灯下草虫鸣”的境界静极,比起评说颇多的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高明多了。殷勤地告诉人们一种境界是怎么来的,往往就达不到这境界,好比一个舞台表演老是用解说词就往往会演不出深刻。还是说王维,后人称赞他“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”,其实诗和画本来就有可以互通的感受。真正的好诗、好画应当是含有“画不出的好画”和“写不出的好诗”。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和蒙娜丽莎庶几近之。
如此看来,诗与画且难互代,何况科学与艺术!话虽如此,但总觉科学工作,一旦沉溺其中,确是时而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受。如果要表达,可能只有借助于诗歌。于是就时时抱着捕捉“科学感受的一刹那”把它写出来的愿望。有过几回尝试,但自觉都不很成功。这里录下一首,且当是当时“少年游”的一个印迹吧!
寻
梦与梦的交替中
你知道我听到了什么
灵魂,灵魂
到夜来更不能隐伏
有如山坳里的泉水
有如手腕上的脉搏
是什么信息
难道我寻到了
曾寻到了
有火一样的酒
熨入血液
半夜里我坐起身来
两手抱我自己的膝
难道这竟是梦你的梦
一个梦
像月光飞入了夜的树林
千万千的形迹
作者简介
王绶绾,生于1923年,籍贯福州。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、名誉台长,中国天文学会名誉理事长。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(院士),历任数学物理学部副主任(1981-1993)、主任(1994-1996)。在提高我国授时精度,创建我国射电天文研究等方面作出贡献。20世纪90年代与苏定强等共创“多天体光谱望远镜”(LAMOST)方案,被列为国家“九五”重大科学工程项目。
相关咨询请拨打400 666 1553(中国)0203 206 1211(
英国) 或发邮件到china@peinternational.co.uk(中国)enquiry@peinternational.co.uk (
英国)